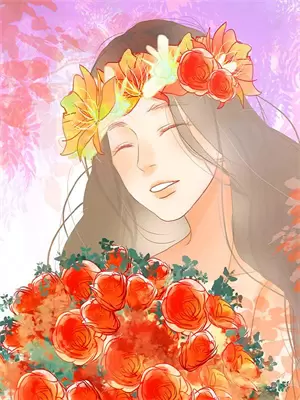
加宽10磅是几厘米
作者: 二棵树其它小说连载
小说《加宽10磅是几厘米大神“二棵树”将地球黎雨作为书中的主人全文主要讲述了:01.我来到地球的时地球已经进入了近月纪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是曾经的80%。这片区域曾经是无人因为人类不习惯这里极度干燥的气人类文明依水而近月纪元之前的人类都习惯于沿水域居那些地方大多气候湿润四季分拥有繁华都市和现在早已湮灭于太平洋海底的残垣断壁大不相让我到这里来的人叫做黎她曾告诉过坐在这片无人区中的雅丹岩能看到地球上最美的星于是我来到了这片雅丹...
01.我来到地球的时候,地球已经进入了近月纪元,
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是曾经的80%。这片区域曾经是无人区,
因为人类不习惯这里极度干燥的气候。人类文明依水而生,
近月纪元之前的人类都习惯于沿水域居住,那些地方大多气候湿润四季分明,
拥有繁华都市群,和现在早已湮灭于太平洋海底的残垣断壁大不相同。
让我到这里来的人叫做黎雨,她曾告诉过我,坐在这片无人区中的雅丹岩下,
能看到地球上最美的星空。于是我来到了这片雅丹区的沙地里,
以人类的样子度过了在地球的第一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地球人视角里的夜空。
月亮看上去很大,如果我对人类视力的估计准确的话,
在人类眼里它大概像一扇敞开在不远处的圆形大门。在它的不远处,还有一颗稍暗的星星,
泛着荧红的光。我忍不住伸出手,隔着三十亿万公里的距离,隔空抚摸它。火星,那是火星。
按时间算,那里应该刚从滔天洪水中平息下来。地球之前,我的上一站便是火星,
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火星。我在未来的火星上遇到了暂居于那里的人类,观察他们,
陪伴他们,最终送别他们。最后一批人类临行前邀请我同行,我婉拒了他们,
说下一站决定去地球看看。
人类表示不解——他们眼里的地球因为月球坠入产生的潮汐力巨变,早已经没有了生命存在。
荒秃秃的一颗土黄色星球,比曾经的火星还要苍凉,实在没什么可看之处。
虽然诞生在火星上,苟活于所谓创世纪元的数十代人类早已习惯了我的存在,
但对于大多数的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邻居,一个他们威胁不了,
但也没有意向干涉人类文明的,平和的邻居。他们没有多问,
我便也没有解释——我要去的并不是他们眼里的地球,我要去曾经的,还有人类居住的地球。
02.决定去地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些不寻常的。首先,“决定”就并非我的行事风格。
而除了“决定”以外,我还进行了“思考”——我为什么去地球?怎么去地球?
到了地球要做些什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在火星上一个被人类称作厄尔皮斯山的地方。
那座山高五千三百米,十公里外有个人类搭建的实验基地。在那里我遇见了黎雨,
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类。那时我停留于火星不久,对此处的观察尚不全面,
而黎雨已经在火星上工作了五年,她正在为人类的创世计划第三阶段工作,
和她所有的同事一样。当时是火星上的夏季。两百年前,
人类通过改变小行星带星体的运行轨迹,引导小行星分批冲撞火星,
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让火星地表温度达到了人类可承受的范围,
夏季的火星最温暖时甚至可达到零下五度。黎雨每天的工作重复性很高,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地失望然后从失望中找出能够自我安慰的地方。有一天,
黎雨在日出之前就出发了,头顶是稀薄到一阵太阳磁暴就能带走的大气层,灰黑色的天空下,
她一个人驾驶着火星车来到3号试验田。试验田里是他们寄予厚望的富氧型植物85号样本,
对着大片看不出颜色枯萎殆尽的植物,黎雨沉默片刻之后便指挥机器人一一移除,
85号样品在火星自然环境里坚持了将近九天,其实和之前的批次相比已经有了些进步。
记录好之后,她又指挥着机器人快速给这片土地种植了一种新的植物,
工作簿上它们的名字——“富氧86号”。大半天迁移嫁接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沉重的防护服让黎雨精疲力尽,她挑了块岩石坐下,休息片刻。
那时的我已经适应了以人类形态的活动,而黎雨也习惯了我这样一个沉默旁观的存在。
于是我来到她身边,在火星的尘土上写了一个问题:厄尔皮斯,为什么。
人类通过输出、接收声音和图案传达信息,二者被称作语言和文字。
而在人类文明的一些分支里,二者有时是分开的两套系统。
这种复杂而模糊的信息传递方式如何支撑这个初具规模的文明顺利运作?
初见之时我对此感到不解。这也是我一开始决定在火星停留的原因。
这座山为什么叫作厄尔皮斯?我的问题是这个。当时的我刚刚接触人类传达信息的方式,
是个初学者。相较语言,我选择从信息传输效率稍高一些的文字切入。黎雨告诉我,
在一个叫做希腊神话的神话体系里,厄尔皮斯是希望的意思。
人类习惯用已知的美好的旧事物来命名新东西,这能帮助他们迅速和新事物产生情感连接,
也能缓解他们对未知的恐惧。恰当的称呼是人类为自己提供安全感的一种方式。
“希望是已知的好东西?”黎雨点点头,说那是最好的东西。相反的,她告诉我,
地球上有一种生物叫做蛇,小时候她对蛇类的恐惧导致她无法将“蛇”这个名称说出口。
现在呢?我在地上这样写。“现在?现在如果一条蛇告诉它能在火星土地上爬五百米,
我愿意让它每天盘在我脖子上睡觉。”然而即使黎雨已经不怕蛇了,
让蛇在火星环境里活着爬五百米在当时还是句梦话。
黎雨每天做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些梦话变成现实。她总是很忙,
忙于培育各种各样有可能适应火星裸环境的生物,经常没有空闲。
在火星上工作的人类都和她一样忙碌,但所有人看上去都很平静镇定,
仿佛结果的失败或者成功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我一开始的确这么认为,
直到后来得知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才明白之所以用同一个表情面对成功和失败,
是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情绪。四个世纪前,地球上一群研究天体物理的人类发现,
漫长的时间里一直以平均每年四公分的速度远离地球的月球突然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轨道偏移。
科学家们依靠月球探测器传回来的大量数据构建出了月球的数学模型,
超级计算机分析后得出结论:月球正在快速靠近地球。按照计算,一千五百年内,
月球将到达地球的洛希极限,整个星体将被地球撕得粉碎,变成地球外侧的一圈行星环。
到那时,地球环境早已因为潮汐力变化而天翻地覆。不幸的是,如果计算结果精确,
人类文明远远撑不到那时。早在月球向地球靠近10%的时候,
大大增强的潮汐力就开始导致海洋每日都向陆地推进,沿海地区地震火山疯狂爆发,
随之而来的海啸将沿海城市吞没。随着时间推进,大海岛消失,内陆山体崩坍,大地撕裂,
固体潮汐高达十几米。当月球靠近到30%的时候,
人类文明便没有了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的可能。
于是全球科学家们经过商讨给出了五百年这个时限,并且在苍茫的宇宙里挑中的火星,
那颗离地球很近的类地行星——五百年,在地球上再没有人类的容身之所以前,
火星必须成为人类的新家。休息间隙,黎雨坐在厄尔皮斯山脚的岩石上,指着赭色的天空,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是一颗泛着微蓝的星星。她展开戴着手套的手掌,
做出了轻轻抚摸的动作。我便知道了那是她的来处。“那是地球,
最近的时候离火星不过六千万公里。”不过六千万公里而已,黎雨却说她不会再回去了,
第三阶段的所有成员出发前都做好了与地球永别的准备。
五百年倒计时让人类迅速摈弃了原本形态丰富的片区管理方式,
奇迹般地成立了地球联合政府,集合人类最优秀的大脑,
制定出了火星改造计划——“创世”。创世计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通过干预类地行星外侧小行星带星体的运行轨道,引导大量小行星分批次撞击火星。
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会使火星温度上升,两极固态冰融化成液态水,火星质量增加,
让大气层达到最基本的稳定;第二阶段,向火星“移植”地球微生物,
被月球“步步紧逼”着的人类拿不出百万年的时间来等待,
基因改造过的光能自养型微生物是地球的第一波“移民”,
它们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完成人类生态环境的奠基工作;第三阶段,种植大量植物,
快速提高空气种的氧、氮含量,繁衍大量的动物,构建抗风险力强的生态系统;第四阶段,
全人类移民。黎雨的工作内容处于第三阶段的初期,按照计划,
这个阶段耗时需要控制在一个世纪以内,
用一个世纪在火星上构建地球花了亿万年才形成的生态环境,成功率低到令人沮丧。
可他们没有时间怀疑,也没有别的选择。在我观察到的阶段里,人类一刻都没有停歇过。
他们总是信心百倍地努力,一段时间后见不到成果,
就像恍然梦醒一般逐渐陷入群体性的迷茫,争端、对立时有发生。
而当争端产生了惨痛的后果,他们的注意力又会回来,
他们会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再次回到一刻不停的努力中。循环往复,无有例外。
看了几轮之后,我难免有些腻烦了。黎雨说,那是因为人是一种很容易死所以很想活的生物。
我猜她的意思是,人类这一切的纠结和矛盾都来源于,他们太容易死亡,
所以太害怕一切让他们死亡的可能。“不用费力了,这不是你能理解的事情。
”黎雨笑着这样说。那时的我已经掌握了人类通用语以及三十多种地区性方言。
不仅以人类的外表示人,
甚至为了一块黎雨递过来的巧克力模拟出了一套人类的消化系统和感官系统,
只是想感受一下她所说的“甜”。她时常感叹我越来越像人类。可是我终究不是人类。
我曾遇见过不少文明,我知道一定程度上变得与文明个体相似是平等理解它们的最佳方式。
我曾为了在一个虫族文明里生活把自己化作虫形。虫族的交流方式就比人类简便很多,
它们通过彼此触碰瞬间实现共享信息,效率上和人类的语言文字比起来高出百倍,
这种信息传递机制我模拟起来也更得心应手。
最后这个文明寂灭于一场覆盖星球每一寸陆地的洪水中。洪水到来之时,
所有失去藏身之处的虫族都遵循着本能就近集合到一起,层层叠叠地抱成一颗球,
以此在浪潮里做最后的挣扎。那样挤成一团情况下,
他们竟然会下意识地避开了我的身体周遭,舍近求远地攀到别的同类身上。
于是我在的那团球比别的球更早瓦解。事实上,
洪水来临之前我在那里以虫形呆了很不短的时间,甚至久于我在火星上和人类度过的日子。
我本以为它们早该习惯了我。但重新理解虫族文明后,我便不敢说理解人类。
以人类的眼光看,我是一个有无限寿命,形态在物质和能量之间转换自如的个体。
强悍的个体,无生无死,这些就决定了我无法共感他们的焦虑和恐惧。但我对此不敢苟同。
随着时间推进,
我常常觉得自己其实能感受到黎雨身上那种鲜少表露出来但一直萦绕不去的忧虑。
那时距离我们初识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黎雨的导师在某次室外作业时因为被变异的植物划破防护服而死于厄尔皮斯的半山腰。
黎雨接替她的导师成为第三阶段总负责人。
实验室里的一个晚上黎雨把我引到一台分子显微镜前。她用平日里的语气让我帮她看个东西。
我凑上去从显微镜里看了一眼,发觉没有什么异样,几条螺旋形的脱氧核糖核酸链而已。
黎雨追问:“如果用你自己的眼睛呢?”“裸眼吗?”我依言离开目镜,伸脖子往镜台上看,
“就一个玻片而已。”我不明所以。她定定地看着我,我以为她要说什么,
等了很久都没听见出声。再转过身时,发现她背对着我站在透明隔墙边,
面对着墙外火星的夜晚,似乎又在找夜空中那颗蓝色的星星。半晌后,
她喃喃地说她没有时间了。我知道她所说属实,
当时第三阶段的任务进度已经比计划慢了十年,加上前面阶段的结果也不理想,
创世计划的最后移民阶段又要后移。那一晚的后面她再没说什么,
和我道别后就锁上了实验室的门独自离开。她离开的背影看上去很低落,
我心知那个夜晚并不寻常,但不知症结在哪里,直到过了很久,
我才意识到她当时真正的、不愿言明的意图。前二十年,
她是火星工作人员里少有的自由乐天派,谈及死亡如同说三餐菜单,
总说些“尽人事听天命”,
“阎王要你三更走不会留你到五更”这种仿佛事不关己的潇洒风凉话。
如果只认识她这个个体,我无法察觉到人类基因里的强大避险本能。
直到那天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人类个体即使克服了对自身死亡的恐惧,
也迈不过延续文明的本能责任感。那座实验室里的她在祈求我,
祈求我能跳出人类框架的本身,给她指引道路。然而当时的我没有懂。我见过那么多文明,
文明的底层逻辑几乎都是将文明延续下去。但我不曾真正属于任何文明集体,
我错过了她隐秘的求助信号。那是既虫族之后,我又一次对某些本质感到疑惑。
但不是对他们,而是对我自己。我隐隐感到,是一种我自认为对黎雨这个人类个体的了解,
影响了我的判断,然后自以为是地将黎雨向我求助的可能性排除出去。
03.黎雨曾与我聊起地球上的时光,
她在一个设立在无人区的训练营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她说虽然当时课程紧张训练严苛所有人都很疲惫,但是心情却放松。“那里什么都好,
只有一点让人讨厌!”说到这个的时候,她经常神气活现。“巧克力不够?
”除了极爱吃巧克力,黎雨并无其他人类概念里的不良嗜好。“是床,训练营的实在太窄,
半夜滚下去一次后我好几次躺在床上都梦见自己趴在悬崖边,睡都睡不踏实。
”她笑着无奈摇头,“就算加宽十厘米也好啊......”这是人类又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文明大难临头之时,还有个体在为自己没有睡好觉感到沮丧。
他们的群体意志下面是一个个看上去混不相关的个体意志。
我以为了解作为个体的黎雨就能了解身在群体里的黎雨。却忘记了作为一个看客,
了解人类群体不代表了解个人,反之亦然。她同我闲谈的时候,
我也偶尔提起经过的那些文明,有些在人类理解范围内,有些或许不在,
她开始还会问出乎我意料的问题,听多了便不再问,只是笑眯眯地听。
有一次听完我说虫族文明水中抱团的事,她问我之后发生了什么。“没之后了,
文明消失后我就离开了那里。”“那种规模的洪水来临前没有预警么,
连你都没有察觉到端倪?”她犹疑地问。“我一早察觉了,但它们并没有。”我如实回答,
当时那颗星体的内部激烈的物质转换过程对于我来说非常明显。她张口结舌地愣了好一会儿,
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一样,终于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我明白了。”我却没明白她明白了什么,
问她什么意思,她也不解释,就是隔着防护服的面罩大笑了两声,冲我挥挥手,
留给我一个跑回实验棚的背影。这个背影和后来夜晚实验室的那个背影之间,
隔了十多年的时间。实验室的夜晚之后,似乎因为接手导师工作的缘故,黎雨比原来更忙。
好几次我去找她,她手头都有一堆事情,于是我们之间少了许多见面的机会。
我开始往厄尔皮斯山的西北边去,火星上别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更习惯我的存在。
与这些人类相处的过程给我补充了许多关于这个文明的认识。作为异类与人类群体相处时,
模仿的相似度是一个需要格外谨慎的东西。不能不像,也不能太像。
全然不像他们会下意识戒备,但如果太像,他们又无法抑制住恐惧。
这方面他们表现得比虫族明显,不如虫族会掩饰,但也比虫族复杂。
说来我能顺理成章地同他们做起相安无事的友邻,还是得益于当时人类并未占领火星,
仍然对火星上的事物都抱有一种小心翼翼、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敏感。











